早春二月,登过山,再游园。穿过一片牡丹花圃,沿山麓幽林小径,寻访林溪精舍。方到溪前,还没来得及领略那清幽胜地,抬望眼,便一下子惊叹于那满目的二月兰了。洞前、坡上、林间,一丛丛二月兰,有如镶嵌山间的蓝翡翠,紫里泛着蔚蓝,蓝里透着雪白,白里又染着淡红,伴着林溪,跳动着音符,欢快着心情。那恣意伸展的四瓣紫花,宛如翩然的双蝶,而六枚微颤的金蕊,俨然是蝴蝶须了。花海中,更兼山林熏染的清气,不由教人神游于彩色雾岚般的梦幻之中。
记得小时候,乡人称二月兰为“诸葛菜”的。每到春天,除了挑荠菜之外,少不了随妈妈去掐诸葛菜。拎只篮子,边走边听妈妈说过,从前诸葛亮率军出征时,见一种菜,称为“蔓菁”,茎叶都能吃,还可制腌菜。于是,诸葛亮命军士广种“蔓菁”。这菜遍植,也就有了诸葛菜的美名。
妈妈带我去的,是离家不远的公园北土山河边。说起公园,那时还是“野”园,既不收门票,也罕见游客,而多见原生的草木。过得拱桥,又一座平桥,沿溪行,绿草如茵的泥土地上似能踩出茵茵春水。步入旧城脚下,虽是山前茀地,但见依水夹岸,松竹并茂,草木葳蕤,姹紫嫣红。诸葛菜长出淡蓝的花蕾,微露一点儿紫色。妈妈说,这是诸葛菜最鲜嫩的时候,在这之前,刚冒头的细芽就掐掉吃,有点太可惜了。但如果再过三五天,花蕾全开,又没那么鲜嫩可口了。脆嫩的诸葛菜,拇指与食指间轻轻一扭,不一会儿,就掐满了篮子,带着一股清甜汁液的气息。饭前,妈妈汲井水洗过,便上灶清炒。做法简单不过,待铁锅里的油烟袅袅升起,菜一倒,“哧啦”有声,急火快炒,加匙盐、糖,滴点醋,便可出锅了。入口,先微微的一点苦,然后是一阵回甘的香,简直妙不可言。就这样,这春馔妙物,一直伴我到外出求学那年。
待我长大了,方知古人早对它青睐有加,且在书页上为之歌唱。只是古今称谓有别,古时称之为葑、须、芜菁、蔓菁等名,而今习称二月兰罢了。唐人韦绚在《刘宾客嘉话录》中说,大诗人刘禹锡曾亦将诸葛菜的好处,总结有六条:“取其才出甲,可生啖,一也;叶舒可煮食,二也;久居则随以滋长,三也;弃不令惜,四也;回则易寻而采,五也;冬有根可食,六也。”想不到,连刘禹锡老先生也是此菜的拥趸者,要不,怎么会如此在行呢?
如今,诸葛菜名不符实了。好像鲜有人吃诸葛菜了,而只赏二月兰了。君不见,每年春,南理工校园的二月兰便成“网红”,一时爆屏。而北大燕园的二月兰,更因季羡林先生的散文《二月兰》,气象独具,名传于世。先生继而睹物思人,充满了对痴爱二月兰的亲人的怀念。不知怎的,同为写二月兰,我却更喜欢宗璞先生的散文《花的话》。她写到:“忽然间,花园的角门开了,一个小男孩飞跑了进来。在那如茵的绿草中间,采摘着野生的二月兰。”想来,这或许是让我找着儿时的感觉了吧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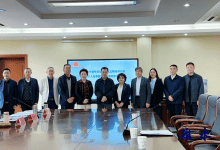

最新评论